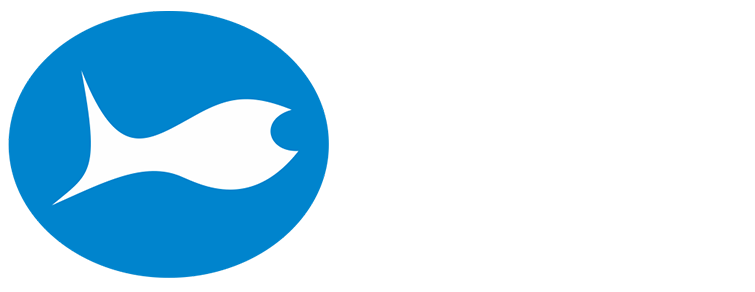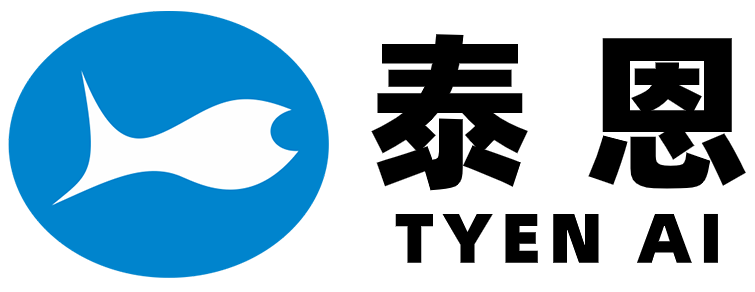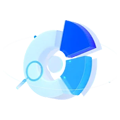新闻资讯
向“电子数据”突围,仍难逃脱物证的“手掌心”
将享有“证据之王”电子证据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以便为电子证据时代提供更好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然而,电子证据目前实际上分属于“视听资料”证据、“电子数据”证据和物证中的电子物证共三个法定证据子类中;并且,还有一些电子证据,如伪基站非法发射的用于传输垃圾短信的电磁波信号,虽然属于关键作案工具性质,但却没有可以明确归属的法定证据种类。
由此看来,现有的法定证据种类划分还有需要改进之处。
一、向“电子数据”突围
1996年,“视听资料”证据正式成为法定证据种类。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为了将如图2-2所示的电子证据作为与物证并列的法定证据种类,人们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激烈的学术争辩,最终发现:(1)可以将图1(a)所示的工具/物品类电子证据划入物证的范畴;(2)图1(b)所示的痕迹类电子证据主要用其中存储的电子数据表达的信息内容作为证据,在此过程中涉及带有思想性的逻辑判断和逻辑转化,这在强调用“客观存在”作为证明材料的物证中是没有的。
于是,选择如图1(b)所示的电子存储介质中存储的电子数据作为(剩余的)电子证据的代表,以(电子数据表达的)信息内容为种差,在法定证据种类划分中以“电子数据”之名与物证并列,并于2012年正式入法。
二、“电子数据”之名存在的不足之处
“电子数据”一词源于信息技术领域,本身并无司法特色,为了避免误解在作为证据种类名称时往往采用“电子数据证据”或“‘电子数据”证据的表述方式。在2012年之后的理论研究和实际使用中,均发现“电子数据”之名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
(1)涵盖范围不当。如:①电子形式的传统证据,如指纹的数码照片、纸质合同的扫描件或数码照片、电子版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等,均是电子数据形式的,但不属于人们心目中正宗的电子证据;②“电子数据”之名天然地含有数字化概念,不能涵盖模拟形式的痕迹类电子证据;③目前的“视听资料”证据基本上是电子数据形式的,在以“电子数据”证据之名提取的电子证据中也有表现形式为“视听资料”形式的,也就是说,“视听资料”证据和“电子数据”证据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等等。
(2)概念混乱,如:①电子数据、表示电子数据的电子信号和表示电子数据的电子信号的物理载体属于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实际上是共同起证明作用的;②电子数据、电子数据表达的信息内容和电子数据表达的信息内容中蕴含的信息内容属于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实际上是共同起证明作用的;③电子数据、电子数据表达的程序代码和电子数据表达的程序代码的运行过程/结果属于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实际上是共同起证明作用的;等等。
(3)犯罪行为人的动作直接导致的是有关物质的存在状况发生变化,并不能直接产生电子数据。这意味着,在电子数据与其要证明的犯罪行为之间,必然存在一层由物质的客观存在和作用形成的物证;而且,在该层物证之中,既有非电子物证又有电子物证(或电子物证成分)。换言之,电子数据并不是最原始、最鲜活的电子证据,只是电子证据中的一个子类。
(4)电子数据,既有存储态电子数据,又有传输态电子数据,而且存储态电子数据大多属于传输态电子数据的转化结果,应客观、公正地将它们均纳入“法眼”之中。但是,要将传输态电子数据纳入“法眼”,就需要有配套的电子信号概念作支撑,否则无法科学、客观、合理地证明传输态电子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换言之,电子数据至少需要与电子信号并列作为电子证据中的子类。
(5)作为电子数据载体的电子存储介质,并不能自主产生能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也就是说,需要将形成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时涉及的电子设备、电子存储介质、电子传输介质和电子信号一并纳入“法眼”之中,才能客观、科学地证明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6)在法理分类中存在归属困难,即:在二分式的证据法理分类中,有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之分。“电子数据”证据显然不属于言词证据;但是,“电子数据”一词的原始含义是指数字电子信号对应表示的信息内容,这与实物证据概念不完全相容。
由此看来,“电子数据”是否适于作为法定证据种类名称,在理论上还值得探讨。
三、难以绕开的物质基础
“电子数据”之名的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在“电子数据”证据的形成和发挥证明作用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促使人们反思以(电子数据表达的)信息内容为种差的合理性。
事实上,世界是物质的,犯罪行为首先导致的是物质的存在状况发生变化,而不是直接产生电子数据和信息,只有“物质的存在状况发生变化”被有关的电子设备转化成电子信号形式并进行逻辑判断处理之后,才会出现电子数据和信息;同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也必须是物质的,而且还要求是可供随时调阅查用形式的。这意味着,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和信息,难以彻底地绕开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物证。
其实,先出现电子设备、后催生出电子证据概念的历史渊源,决定了电子证据与物证之间必定有不解之缘。因此,提及电子证据就直接想到“电子数据”证据,认为“电子数据”证据是电子证据的同义语或代名词,认为电子证据是“电子数据”证据的简称,此类现象和学术观点多少有些不妥;换言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30余年的发展,人们对电子证据的认知似乎出现了某种偏差,从最初认识到的有模拟形式和数字形式的电子证据到现在的几乎言必谈“电子数据”,似乎忽略了电子证据天然具有的物证属性。
由此启示我们:要想继续践行“将电子证据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的初心,就需要寻找到新的划分特征,如以物质基础和形成机理为划分特征,既将那些电子形式的传统证据排除在外,又能精确地涵盖人们心目中正宗的电子证据,还能清楚地区别于实物物证。
提示:本文是基于作者所著电子证据理论三部曲,《电磁波证据原理》、《电子证据理论重铸研究》,《电子证据导论》,其中有关章节的学术观点原创性写作而成,所有权归作者所有,文责也由作者自负。请尊重原创性写作的不易,如需引用,烦请标明出处!
如果您认可本文的观点,或是觉得本文的内容足够专业和中肯,请您动动指哪打哪、点石成金的手指,给本文点赞、推荐和分享,更欢迎您关注和加粉周工解证。
上一页
下一页